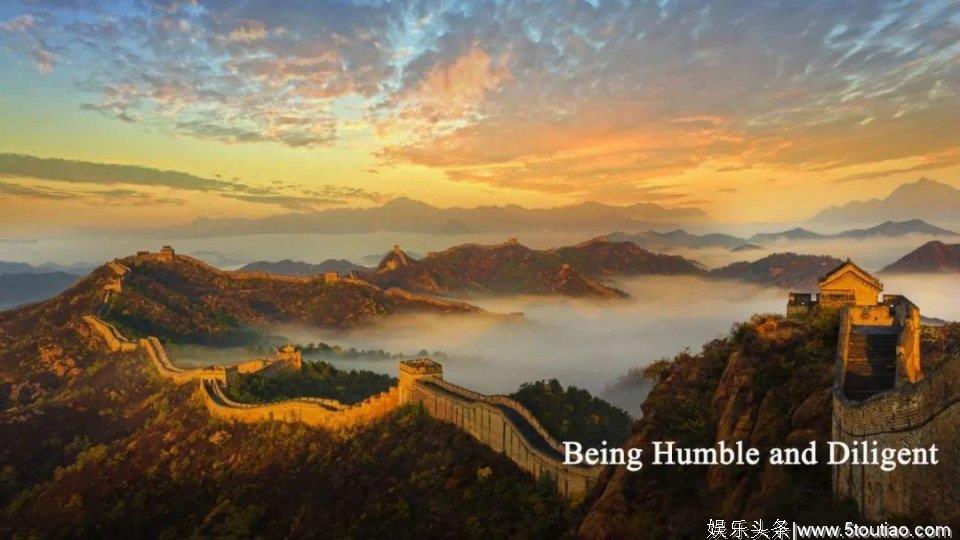
导 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关注了ICSID最近登记的日本投资者Macro Trading Co., Ltd.对中国政府提起的投资仲裁案件,并以其援引的1988年《中国和日本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China-Jap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简称“中日BIT”)简要分析了该案可能涉及的管辖权范围。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中日之间除了这一双边投资协定之外,还与韩国在2012年签署了《中国、日本及韩国关于促进、便利及保护投资的协定》(China-Japan-Korea Tr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以下简称“中日韩TIA”)。那么中日BIT与中日韩TIA在对投资者的保护方面有什么区别?各自所规定的争议解决机制有哪些不同?作为两个在时间上先后订立且都有效的投资协定,在具体案件中又应当如何适用?
就两个协定所保护的投资范围而言,中日韩TIA所受保护的投资范围更广、类型也更为明确,直接针对“投资行为”本身。其第1条第1款明确规定“‘投资’一词是指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具有投资性质的各种财产,例如资本或其他资源投入、收益或利润预期或风险承担等,投资的形式可能包括:(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同时涵盖了“投资孳息”。而中日BIT则是从投资财产和收益的角度,对投资涉及的财产性权利进行了概括。其第1条第1款约定:“‘投资财产’,系指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在进行投资时,依照或不违反该缔约另一方法律和法规用作投资的所有种类的资产,包括:(1)股份和其他形式的公司份额……”。
一、ISDS机制的区别
中日BIT与中日韩TIA各自建立的ISDS(Investor-State Dispute Resolution)机制,虽然都以条约协议的方式确认了ICSID仲裁庭的管辖,但在具体程序方面的规定则迥然不同。
前置程序
投资者若援引这两个条约将争端提交ICSID仲裁庭解决,都需要满足与东道国提前协商的前置程序要求。中日韩TIA的第15条第2款规定:“任何投资争议应尽可能通过作为投资争议当事方的投资者(以下称“争议投资者”)与作为投资争议当事方的缔约方(以下称“争议缔约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书面协商请求应由争议投资者在投资争议提交本条第三款规定的仲裁之前提交给争议缔约方。”
同样,中日BIT第11条第2款也约定了“缔约任何一方或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其他承担补偿义务者和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关于第五条第三款所述的补偿价款的争端,如果当事任何一方提出为解决争端进行协商的六个月内未能解决,则根据该国民或公司的要求,可提交参考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称“华盛顿公约”)而组成的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缔约任何一方和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关于其他事项的争端,可根据当事双方的同意,提交如上所述的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如果该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该缔约一方境内求助于行政或司法解决时,该争端不得提交仲裁。”
在前置程序的协商时间方面,中日BIT规定了不少于六个月的协商时间,而中日韩TIA则约定了较短的协商时间,“投资争议不能通过第11条第2款所指的协商在书面协商请求递交至争议缔约方之日起四个月内解决”且符合“关于本国行政复议程序(如适用)的要求”。在此方面,新协定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保护,但同时也可能削弱东道国当地行政复议程序的实际作用,从而使得前置程序的目的不能实现。
中日韩TIA在书面协商请求方面也设定了更为详细的要求,例如书面请求需载明“争议投资者的名称及地址”、“主张的本协定项下被违反的义务”、“投资争议事实简述”、“寻求的救济以及大致的损害赔偿金”等,同时列明了东道国接收请求的主管机关,即实质上明确增加了一项前置程序:向东道国提交符合形式的书面协商请求。这一要求从形式上,却更有利于促使投资者通过当地救济的途径解决争议。
“岔路口”条款
中日韩TIA第15条第5款规定:“争议投资者一旦将投资争议提交争议缔约方的管辖法院或本条第三款规定的仲裁之一,则争议投资者所做选择应当是终局的,争议投资者之后不得再将同一争议提交本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仲裁”。
这一“岔路口”条款(Fork-In-The-Road Clause),要求投资者在东道国国内救济和国际投资仲裁中二选一,一旦选定则为终局。此类条款的设计有利于防止投资者滥用权利,确保投资争端解决的终局性和有效性,在实务上节约了救济资源,在法理上也符合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
同样,中日BIT第11条第2款中规定:“如果该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该缔约一方境内求助于行政或司法解决时,该争端不得提交仲裁。”(“In the event that such national or company has resorted to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settlement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latter Contracting Party, such dispute shall not be submitted to arbitration”.) 相比于中日韩TIA,这一条款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投资者的选择是终局的,但实质上也起到了“岔路口”条款的作用。
当然,基于长期投资活动涉及的复杂情形,在适用“岔路口”条款时,需要先判断涉案争议是否为“同一争议”。而这一争议焦点的解决往往取决于仲裁庭对此类条款是否会采用更为宽松的解释方式。与此相关的分析,可以参考我们的另一篇文章:国际投资仲裁中岔路口条款的适用[1]。
管辖权
正如我们曾经讨论的,中国订立的第一代双边投资协定,投资者一般只能就涉及征收赔偿金额产生的争端提交投资仲裁。而结合中日BIT第11条第2款的具体内容来看,该条款所述“与征收赔偿金额有关的争议”应当仅指第5条第3款所明确的“补偿金额能否使投资者恢复至未被征收以前的财政状况”、“补偿是否迟延支付”以及“补偿是否能够有效地兑换和转移”相关问题。因此,中日BIT项下,缔约方仅同意就关于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效果的措施的补偿价款争端提交ICSID管辖。但中日韩TIA在投资争端的类型方面,则没有进行限定。
诉讼时效
中日BIT中并无诉讼时效条款,但中日韩TIA的第15条第11款中,对于诉讼时效有明确的规定,即诉讼时效为自投资者首次知悉或应当首次知悉损失或损害后的三年:“尽管有本条第三款的规定,如自争议投资者首次获悉或者应当首次获悉(以较早时间为准)其遭受了本条第一款所指的损失或者损害之日起已超过三年时间,则不能提交本条第三款规定的仲裁。”该规定限制了投资者基于条约的请求权,对怠于行使权利的投资者减少了保护,从而节约了国际投资仲裁层面的救济资源。
二、中日、中日韩投资协定的适用
中日BIT与中日韩TIA都约定ICSID对其项下投资的争端有管辖权。由于中日韩TIA并没有替代缔约三国在此条约生效前订立的其他投资协定,那么如果同一案件中涉及此类先后订立的投资协定时,ICSID仲裁庭又应如何适用?有关这一问题,平安保险诉比利时案(Ping An Insurance v. Belgium[2])(以下简称“平安案”)的仲裁庭,分别从条约溯及力、临时管辖权、缔约方意图等各个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虽然仲裁庭在条约解释上有不合理之处[3],但确实为此类涉及两个中国投资仲裁协定的案件,提供了清晰地裁决思路。因此,本文就主要从平安案的角度,简要分析如果一个案件同时涉及中日BIT与中日韩TIA这两个投资协定,ICSID仲裁庭可能考察的因素。
从2007到2008年4月,平安集团通过收购富通集团价值约20亿欧元的股票,成为富通集团的单一最大股东。2008年,比利时政府与巴黎银行达成一项股权互换协议,使得富通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业务被完全剥离。比利时政府后购买并转售富通银行股权,并规定居住在欧盟境内的投资者可以分享比利时政府转售中所获得的溢价收益,但是作为富通的单一大股东平安集团却无权获得赔偿。2012年9月,平安集团在多次与比利时政府沟通无效后,选择依据中国和比利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向ICSID提起仲裁。平安案中涉及的两个投资协定为1986年中国-比利时与卢森堡经济联盟BIT与2009年中国-比利时与卢森堡经济联盟BIT。申请人平安集团在管辖权问题上依赖于2009年的中比BIT,在实体问题上则依赖于1986年的中比BIT。
协定的有效性
首先,仲裁庭会结合后订立的投资协定的具体内容,分别判断两个条约的有效性。仲裁庭会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第30条就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Application of Successive Treaties Relating to the Same Subject Matter)的规定:“遇条约订明须不违反先订或后订条约或不得视为与先订或后订条约不合时,该先订或后订条约之规定应居优先。遇先订条约全体当事国亦为后订条约当事国但不依第五十九条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之范围内适用之”,以此在条约间不冲突的范围内,协调地同时适用两个条约;在条约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后订立的条约内容[4]。
本案项下,具体到中日BIT,其第15条规定该协定有效期为十年,十年以后,除非缔约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协定,协定继续有效。同样,中日韩TIA的第27条规定,该协定有效期也为十年,且此后除了缔约一方提前退出的情形外“应继续有效”。第25条也明确规定该协定与其他协定的关系“本协定的任何条款均不影响缔约一方在该缔约方与缔约另一方达成的、在本协定生效日存在且有效的任何双边投资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包括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的相关权利和义务。”
因而,可以确定,两个投资协定皆为生效协定,且中日韩TIA没有替代中日BIT。所以,如果二者的规定没有冲突时,则应当同时协调适用;如果产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中日韩TIA。而中日韩TIA第25条同时注明“各方确认,当缔约一方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发生争议时,本协定的任何条款均不得解释为阻止投资者依赖该缔约双方达成的、投资者认为比本协定更优惠的双边投资协定。”因此,即使优先适用中日韩TIA,投资者也可以主张适用两个条约中,其认为对自己而言更优惠的规定。
新条约的适用范围
在判断新协定适用范围的问题上,平安案中的仲裁庭援引了维也纳公约第28条(non-retroactivity of treaties)所确定的条约不溯及既往原则。具体为:“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国生效之日以前所发生之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已不存在之任何情势,条约之规定不对该当事国发生拘束力。”仲裁庭无疑都肯定条约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但同时提出条约及其规定是否有溯及力取决于缔约方的意图。这一推定由ILC对维也纳公约草案的评述[5]所确认,另外被许多仲裁庭所确认,如Impregilo v. Pakistan[6]、SGS v. Philippines[7]。
但平安案的仲裁庭明确区分了新条约的过渡/临时管辖与溯及力,同时结合缔约方订立条约时的意图,根据2009年中比BIT的第10条第2款“本协定应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所有投资,不论其是在本协定生效之前还是之后作出的。但是,本协定不得适用于在本协议生效前已进入司法或仲裁程序的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索偿”,认定2009年的BIT适用于中比之间所有的投资。但是,仲裁庭最终采用Jan de Nul v. Egypt案[8]与Walter Bau v. Thailand 案[9]的观点,认定2009年中比BIT保护条约生效前的“投资”不等同于适用条约生效前的“争议”,本案的争议属于在2019年的条约生效前,就已进入司法或仲裁程序的争议,不能适用2009年中比BIT。因而否认了ICSID对平安案的管辖权。
从条约文本内容上看,2009年中比BIT、2012年的中日韩TIA均规定,保护生效前的“投资”,但不包括生效前的“争议”,此类规定在原则上异曲同工,但适用时也有不同之处。2009年中比BIT 第20条第2款规定:“本协定应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所有投资,不论其是在本协定生效之前还是之后作出的。但是,本协定不得适用于在本协议生效前已进入司法或仲裁程序的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索偿”。而2012年中日韩TIA第27条第2款规定“本协定也适用于任何缔约方投资者在本协定生效之前根据缔约另一方的适用法律法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获得的所有投资”;但第7款又明确表示“本协定不适用于在本协定生效前发生的事件引起的权利请求,也不适用于在本协定生效前已解决的权利请求”。原则上,二者都保护生效前的投资,且都区别了投资与投资引起的争议;但中日韩TIA排除的适用对象为:2014年5月17日(该协定正式生效的日期)之后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权利请求”(claims),并未以争议是否进入司法或仲裁程序为区分标准。因此,其实质上比平安案中被排除的新协定“生效前已进入司法或仲裁程序的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索偿”范围要更广。
结 语
中日BIT与中日韩TIA都是持续有效的投资协定。但由于他们各自设置的ISDS机制有诸多不同,如果案件同时涉及这两个协定时,争议双方应当准确掌握他们各自的特点与相互之间的关系。
以平安案为例,平安集团仲裁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不够了解新旧协定之间的关系,完全依赖于新BIT而放弃引用旧BIT主张管辖权。而仲裁庭甚至也认为平安集团可以继续在旧条约下提起诉讼或仲裁,因为新条约有意没有对旧条约项下未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的争议作出处理。
再以日本投资者Macro Trading Co., Ltd.对中国政府提起的投资仲裁案件为例,ICSID的登记显示,投资者在申请仲裁时只援引了中日BIT。那么是否意味着申请人在后续程序中,就不能再要求适用中日韩TIA?或者进一步而言,对于申请人在前置程序的磋商请求中没有提出的请求,仲裁庭有是否有管辖权?
有关上述问题,在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件文件时,无法研究可行的答案。但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在案件处理中,却逐渐倾向于给予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更广泛的职权范围。在加拿大-民用飞机补贴案中[10],加拿大政府就曾依据DSU第6条第2款规定的“设立专家组的请求应……确认争论中的措施并提供一份足以明确陈述问题的起诉的法律根据概要”与SCM协定第4条第2款规定的“提出的磋商请求中应包括一份关于补贴存在和性质的现有证据的说明”,申辩巴西政府不能在后续程序中提出磋商申请书以外的请求或者援引请求书之外的法律。这一抗辩的理论基础是英美法中传统的禁止“突袭式裁判”原则(“trial by ambush”),加拿大政府同时还引用了Brazil - Desiccated Coconut[11]案与European Communities - Bananas案[12],但都被专家组驳回。专家组认定:SCM协定对磋商请求书的详细要求,是为了避免前置程序形式化,而不是限制专家组的管辖权;另外,根据DSU第7条第2款规定的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专家组有权通过审查设立专家组的请求书等文书,确定涉案争端的具体争议点。只要争端没有超出请求书的范围,专家组就应当有管辖权[13]。
基于ICSID仲裁规则的第42条第4款之规定[14],仲裁庭有权通过审查争议双方提交的意见(“submissions”)来确定其管辖权,并没有对这些意见的具体形式进行限制,因此即使申请人当前在仲裁申请书或者磋商协议等文件中只援引了中日BIT,也可能很难以此来排除其在后续程序中适用中日韩TIA。
综上,多个投资协定可能同时适用的案件中,投资者在提出请求时,需要重视每一个程序环节,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如何制定对己方更为有利的仲裁策略;相应地,东道国也需要更为了解其缔结的新旧条约之间的差异,提前作出应对方案,争取在程序方面取得更为有利的结果,从而尽早解决争议。
参考文献
[1] 参见环中投资仲裁文章:投资仲裁 | 国际投资仲裁中岔路口条款的适用
[2]Ping 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Limited and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mpany of China, Limited v. Kingdom of Belgium, ICSID Case No. ARB/12/29.
[3]Chunlei Zhao, Jurisdiction Ratione Temporis in Successiv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What Can Chinese Investors Learn from the Ping An Case? China & WTO Rev. 2017:1; 61-90, p 81.
[4]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pplicable Law and Liability in Electrabel S.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7/19, 4.143-4.167.
[5] ILC Yb 1966, II, pp 211-212.
[6] Impregilo v. Pakistan 311.
[7] SGS v. Philippines 166.
[8] Jan de Nul N.V. and Dredging International N.V.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ICSID Case No. ARB/04/13.
[9] Walter Bau AG (in liquidation) v. Thailand (UNCITRAL), Award, July 1, 2009.
[10] Canada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Export of Civilian Aircraft (1999) WTO Doc. WT/DS70/R, Panel Report.
[11] Brazil - Measures Affecting Desiccated Coconut (Complaint by the Phillippines) (1997), WTO Doc. WT/DS22/AB/R.
[12] European Communities - 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 (Complaints by Ecuador, Guatemala, Honduras, Mexico, United States) (1997), WTO Doc. WT/DS27/ECU.
[13] Canada Case supra note v, para. 9.11-9.12.
[14] Rule 42(4) of ICSID Arbitration Rules 2016, “The Tribunal shall examin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entre and its own competence in the dispute and, if it is satisfied, decide whether the submissions made are well-founded in fact and in law. To this end, it may, at any stage of the proceeding, call on the party appearing to file observations, produce evidence or submit oral explanations”.
信息源于:环中投资仲裁 ,作者环中争端解决团队


